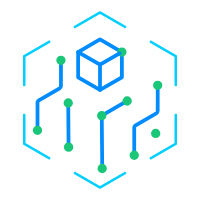宁乡厨师帮海外吃香厨师长6年赚回1万
宁乡厨师帮海外吃香厨师长6年赚回1万

“宁乡厨师帮”海外吃香海外淘金收入赛金领;从20世纪年代至今,已有上千名宁乡厨师为赚“外快”漂洋过海,足迹遍布德国、日本、越南、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郝厨师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宁乡厨师”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劳务输出品牌。……
这是一场异常考验观众唾液腺的比赛:在来自南非国际华人区各大酒楼、食肆的名厨们巧手翻飞下,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争相呈上……最终,在现场众多“洋巨人”的簇拥下,一名小个子摘得了最后的金-ad厨师机湖南长沙宁乡人陈学冬用自己的绝佳创意与烹调技术,不仅征服了现场评委,更证明了:真正精湛的厨艺无关国界!
而陈学冬的打拼经历仅仅只是“宁乡厨师帮”征战海外的一道缩。该县商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世纪年代至今,已有上千名宁乡厨师为赚“外快”漂洋过海,足迹遍布德国、日本、越南、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父亲是厨师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宁乡厨师”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劳务输出品牌。
打个“飞的”去开工,如今早已经不是什么明星大腕、高知白领的专利,在中国内陆省份湖南的一个普通小县城里,一群整日围绕灶台打转的普通农民工也过上了这种洋气十足的“现代职场生活”。并且,与某些所谓“人才”的“镀金式”留洋不同,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出国掘金,带回的财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品这些新时代农民工的故事,尽管过程并不轻松,尽管“口感”五味杂陈,却与他们在异国他乡烹制出的道道佳肴一样活色生香。
“在南非干了5年,存下万,回来后买了房子又开了店……”3月24日,当今日宁乡话厨师宁乡话厨师上陈学冬时,他正趁着久违的好天气,在郊外踏青游乐。名下店铺每月可观的营业收入让现年岁的陈学冬提前过上了惬意的“退休生活”,而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14年前的出国务工经历。
19年,陈学冬高中毕业,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厨师行业继续学习。在长沙商业技校,刻苦用功的陈学冬是当年的厨师刀功毕业生之一。出校门后,他又拜了“宁乡四大名厨”之一的郭庆献为师,厨艺进步神速。
郭庆献堪称“宁乡厨师帮”出征海外的“开山鼻祖”,19年,他第二次回国后,向陈学冬感慨道:“你学厨有18年了吧,该到外面去看看了,不仅挣得更多,也能增长见识。”深受启迪的陈学冬没有迟疑,当年就与另一个宁乡小伙一道,登上了前往南非的飞机。
“我进入到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旗下的天厨大酒店作厨师,起初工资为每月0美元-厨师吴国红得知这个数字时,我线元人民币呢!试想,当时国内有多少人能拿到00元的月工资?”这还只是开始,升任厨师长后,陈学冬的月收入涨至100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还不愁吃住。“酒店主要经营豪华自助餐,每天,鲍鱼、鱼翅、海参、燕窝总会剩很多,我们几十个厨子哪吃得完啊!”
酒店提供的住所,更是让刚刚从宁乡乡下简陋砖瓦房里走出来的陈学冬有如梦似幻之感:140多平方米的大洋房,有5个装修豪华的房间供他使用;外围是个占地2000多平米的院子,配备有花园、泳池……“别看工资高、吃住条件好,活却并不很累,每天做10小时,每周星期一休息一天。”
但异国并不是天堂,再优渥的物质条件,也抵消不了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与憋屈。
“你这么矮,能干什么?快回家吧!”在陈学冬的记忆中,当时的酒店经理曾多次用蹩脚的中文“劝退”自己,“我只有一米六,在所有厨子里是最矮的,而且人又瘦-厨师染头发经理认为厨师是体力活,必须体格高大才能胜任。”
“当时,我心里那个憋屈啊,真是很难形容。”但陈学冬深知,光生气没用,唯有苦练厨艺,等待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那边流行吃海鲜,这对于以前在湖南很少接触海鲜类食材的我而言是个弱项,只能花比别人更多的气力来刻苦钻研。”
19年,陈学冬的机会来了-招聘厨师网南非国际华人区举办了一场厨艺比赛,由他精心设计、分别以鲍鱼和螃蟹为主要食材的“君临天下”与“红袍加身”两道菜品,一举摘得金。“一位外国评委冲我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赞:‘中国人很棒!’……”事隔多年回忆起来,陈学冬依然兴奋。
“刚到南非的头两年,我只会说糖、盐、油等工作中最常用到的英文单词。语言不通让工作开展得很艰难,甚至闹过笑线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举办酒会,邀请了几十位外国大使前来赴宴,而这是他大唐厨师味业次做主理,非常紧张。当时,陈学冬吩咐自己的非洲徒弟做肉脯,“估计是我说错了单词,结果他做了个水果拼盘摆在肉类区。事后经理把我训了一顿,还责令我公开检讨”。
但最难的还不是语言关,而是旁人歧的目光,“比如,我们去餐馆吃饭,那些白人看到我们就会走开,因为觉得我们又吵又脏”。甚至去邮局寄信,一些白人都不愿意在有华人的队伍里排队。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曾有段时间,每次看到女儿,陈学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这句诗-德州招聘厨师主人公“儿童”即自己的女儿,而比诗中所写更甚的是,“笑问”变成了“哭着挣扎”。
“那几年远离亲人,身边又没什么朋友,晚上一个人睡在又空又大的房子里,常常会莫名地想哭。”谈话进行到这里,陈学冬突然短暂沉默,之后继续讲述,“我老婆在家乡做建材生意,交际面比较广,我一走五年,说一点不担心是假的。”为给妻子一些念想,与通电话相比,陈学冬更喜欢写信,但每封信从南非到中国宁乡至少要“走”两个星期,一来一回的,一个月就过去了。
“我最对不起的还是女儿,她当时才七八岁,刚懂事就长时间见不到爸爸。”到南非满三年后,陈学冬才回过一次家,却没能如愿盼到女儿的笑脸,连收到的眼神都是冷冷的。又过了两年,陈学冬合同期满,正式回国,“我高兴地一把抱起女儿,她却拼命挣扎哭闹,像是完全不知道我是谁……直到现在,女儿和我都不亲,不管我怎么和她套近乎。有关她的事情,我总是得通过她妈妈才能知道”。这是陈学冬心中永远的疙瘩。
综合五年中的见闻与得失,陈学冬从不讳言那几年为自己的如今打下了经济基础,却仍旧执著地认为:“人,一定要叶落归根。”